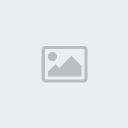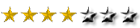人有生老病死、旦夕祸福,树同样有,但如果没有毁灭性的天灾人祸,树却能站立几百年,甚至更久,为一代代人撒下片片斑驳的绿荫。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就有这么一棵树,仿佛长在一座荒芜的孤岛上,随着记忆的浪潮,向着远方越摇越远,由清晰渐渐变成小小的一点,它成了一个特别的存在,一个绿色的符号,生长在我的记忆深处,不老不死,不伤不灭,一直绿意盎然地活着。
这棵树的树龄有将近五百岁,树种为黄果树,这棵树原本是一棵祈愿树,种在一座小庙中,受烟火熏染,受信男信女跪拜,不知闻经参禅多少年,也不知道促成了多少桩金玉良缘,又实现了多少个甜蜜心愿,后来小庙几经辗转改成了一所幼儿园,而我有幸成了其中一员,想到此处,就有些感慨,仿佛前世今生都早已安排,注定我此生与佛有缘,小时候奶奶将我引进佛教,又在我出生那天,梦见了送子观音托梦,后来又进入金顶寺旧址上幼儿园,这一环扣一环,竟让我与佛教结下了不解的情缘。
记得小时候,每逢课间休息,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朋友,就绕着黄果树追逐打闹,累了就靠着大树歇息,秋季黄果树会开满淡淡的黄花,花瓣有一种淡淡的酸甜味,我们有时会捡起一片或者两片塞进嘴里,感受酸酸甜甜的味觉体验,就像吃零食般畅快。放学后,总跑到黄果树下找奶奶,奶奶总坐在树下等孙儿,她安然地坐在华盖田田的黄果树下,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大衣,满头银发在树荫婆娑中显得特别明丽,仿佛一位睿智的菩萨正在树下打坐参禅,奶奶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,和蔼的双眸,幸福地望着一群小朋友在沙堆里追逐嬉戏,那份悠然恬静能融化所有凌冽的坚冰,我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,顺手捡起几片落下的黄果树叶,就拉着奶奶欢欢喜喜地回家去,那份美好与甜蜜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记得有一年,幼儿园计划扩建,打算把黄果树砍去,可施工队刚刚砍下一根树根,砍树人就一病不起,寻遍名医都无方可医,无奈之下只得请来法师,法师给黄果树烧完香、挂了红布、又放了鞭炮,那人的病才渐渐好转,至此再也没有人敢打这棵树的主意,同时这棵树也被尊为了神树。
还有一回,一只狗般大小的猫头鹰,停在黄果树上久久不肯离去,仿佛黄果树长了一对幽深的眼睛,这一场景很多人都见过,其中也包括我,至此黄果树的神秘又加重了一层。
后来,我兜兜转转离开了故乡,十多年后,才重归故里,有一次闲暇,上街游玩,转着转着就来到了儿时读书的幼儿园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,迈进了锈迹斑斑的大铁门,万万没想到幼儿园已经拆毁,空落落地留了一地瓦砾和碎石,而那棵黄果树依然伫立在清风里,笑对时光的流逝,而在树身上多了一个蓝色的牌子,上面简单地写着:保护树,林业局签发,也不标明树龄,也不说明树种,只单单这几个字就草草了事,如此不负责任,让我这想了它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未免有些心疼,但转念一想,这些浮华的名分,对于一棵活了几百年的大树又算得了什么呢?
我站在树下,望着这棵依旧繁茂的黄果树,感慨良多,以前坐在树下等孙儿的奶奶已经入土,个子小小的男孩已经英英玉立,而不变的你,依然精神矍铄地站成了一道风景,时光飞逝,沧海已变桑田,而终究有些生命在时间的夹缝中生存下来,比如说你——敬爱的树爷爷。生命就是这般奇妙,在我们感慨年颇老矣时,而树却以另一种形式站成永恒。究竟这份痴痴的等待为了谁呢?我想只有树知道。
神器在手,论坛有我.君笨笨为你服务.
在我的童年记忆中,就有这么一棵树,仿佛长在一座荒芜的孤岛上,随着记忆的浪潮,向着远方越摇越远,由清晰渐渐变成小小的一点,它成了一个特别的存在,一个绿色的符号,生长在我的记忆深处,不老不死,不伤不灭,一直绿意盎然地活着。
这棵树的树龄有将近五百岁,树种为黄果树,这棵树原本是一棵祈愿树,种在一座小庙中,受烟火熏染,受信男信女跪拜,不知闻经参禅多少年,也不知道促成了多少桩金玉良缘,又实现了多少个甜蜜心愿,后来小庙几经辗转改成了一所幼儿园,而我有幸成了其中一员,想到此处,就有些感慨,仿佛前世今生都早已安排,注定我此生与佛有缘,小时候奶奶将我引进佛教,又在我出生那天,梦见了送子观音托梦,后来又进入金顶寺旧址上幼儿园,这一环扣一环,竟让我与佛教结下了不解的情缘。
记得小时候,每逢课间休息,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朋友,就绕着黄果树追逐打闹,累了就靠着大树歇息,秋季黄果树会开满淡淡的黄花,花瓣有一种淡淡的酸甜味,我们有时会捡起一片或者两片塞进嘴里,感受酸酸甜甜的味觉体验,就像吃零食般畅快。放学后,总跑到黄果树下找奶奶,奶奶总坐在树下等孙儿,她安然地坐在华盖田田的黄果树下,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大衣,满头银发在树荫婆娑中显得特别明丽,仿佛一位睿智的菩萨正在树下打坐参禅,奶奶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,和蔼的双眸,幸福地望着一群小朋友在沙堆里追逐嬉戏,那份悠然恬静能融化所有凌冽的坚冰,我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,顺手捡起几片落下的黄果树叶,就拉着奶奶欢欢喜喜地回家去,那份美好与甜蜜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记得有一年,幼儿园计划扩建,打算把黄果树砍去,可施工队刚刚砍下一根树根,砍树人就一病不起,寻遍名医都无方可医,无奈之下只得请来法师,法师给黄果树烧完香、挂了红布、又放了鞭炮,那人的病才渐渐好转,至此再也没有人敢打这棵树的主意,同时这棵树也被尊为了神树。
还有一回,一只狗般大小的猫头鹰,停在黄果树上久久不肯离去,仿佛黄果树长了一对幽深的眼睛,这一场景很多人都见过,其中也包括我,至此黄果树的神秘又加重了一层。
后来,我兜兜转转离开了故乡,十多年后,才重归故里,有一次闲暇,上街游玩,转着转着就来到了儿时读书的幼儿园,我怀着激动的心情,迈进了锈迹斑斑的大铁门,万万没想到幼儿园已经拆毁,空落落地留了一地瓦砾和碎石,而那棵黄果树依然伫立在清风里,笑对时光的流逝,而在树身上多了一个蓝色的牌子,上面简单地写着:保护树,林业局签发,也不标明树龄,也不说明树种,只单单这几个字就草草了事,如此不负责任,让我这想了它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未免有些心疼,但转念一想,这些浮华的名分,对于一棵活了几百年的大树又算得了什么呢?
我站在树下,望着这棵依旧繁茂的黄果树,感慨良多,以前坐在树下等孙儿的奶奶已经入土,个子小小的男孩已经英英玉立,而不变的你,依然精神矍铄地站成了一道风景,时光飞逝,沧海已变桑田,而终究有些生命在时间的夹缝中生存下来,比如说你——敬爱的树爷爷。生命就是这般奇妙,在我们感慨年颇老矣时,而树却以另一种形式站成永恒。究竟这份痴痴的等待为了谁呢?我想只有树知道。
神器在手,论坛有我.君笨笨为你服务.